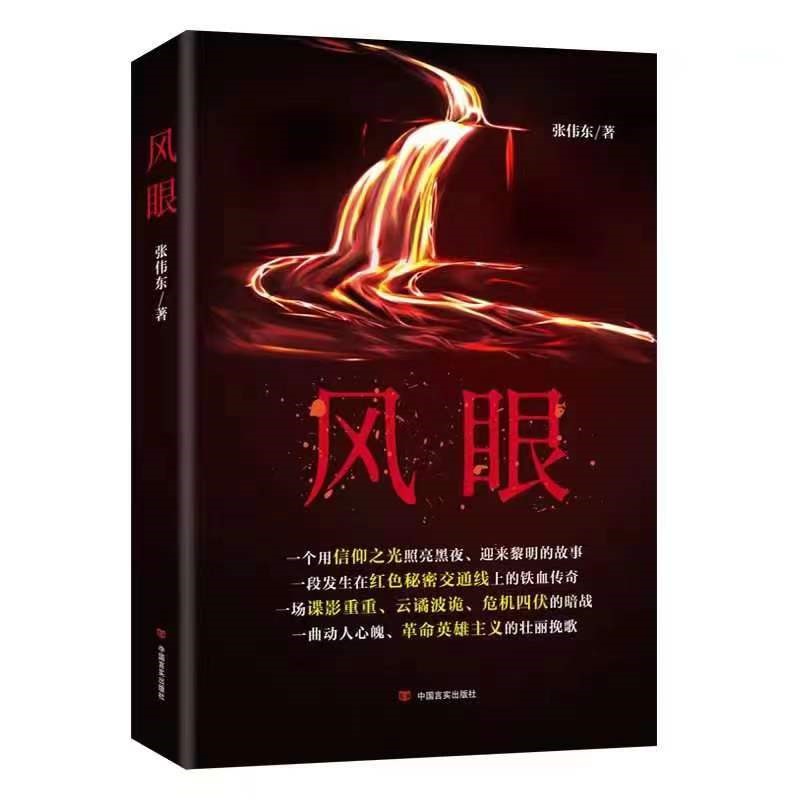
同样用文字的方式表述,历史相对于小说,是抽象的,编年体事件随时间行进秩序而罗列的文本,只是一些筋骨。而小说则是有筋骨,有血肉,有情感,有意蕴与内涵的文本。当然,这是两类文体,彼此差别很大。但随着历史与小说的结合——历史小说题材进入读者的视野,云烟般的历史则在我们眼中清晰可感起来。正是历史小说这种有血有肉有意味的文学形式,给了历史一具鲜活的肉身。
张伟东的长篇历史小说《风眼》,耗费三年多的时间完成,长达30多万字。关于历史小说的阐释,网上有如下一段资料文字:“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描写主题的小说。它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这类作品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历史根据,容许适当的想象、概括和虚构,主要目的在于给读者以启示和教育。这段文字虽然解释简单,但还是说出了历史小说的基本面貌。历史小说,从小说起源时就有,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现代作家姚雪垠著的《李自成》也是历史小说。当下,一些穿越历史朝代戏说性质的网文小说,却不能定位为历史小说。这其中缘由是对历史真实有多大程度的承传问题起区分作用,在历史小说中,作家的历史意识及其历史观必须严谨客观。
《风眼》的写作背景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俄边境城市绥芬河。故事围绕国际秘密交通线特定的历史事件展开,表现了革命者赵兴东短暂而传奇的战斗人生。《风眼》依据历史史实和真实人物创作,整部小说布局谋篇精炼,故事框架构建有序,事件层层深入,情节引人入胜,细节鲜活充盈,叙述环环相扣,行文逻辑缜密,是一部集悬疑、谍战、战争性质为一体,内容起伏跌宕,摇曳多姿的历史传奇小说。
历史是要写实的,小说则是虚构的。历史小说,要在写实和虚构之间跳舞,过于写实,可能失之小说的文学性味道;过于虚构,可能又脱离了历史的真实性。写作历史小说,需要尊重历史大环境的真实,需要尊重历史空间与时间的真实,需要大量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需要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细节,需要还原历史中人物的风貌和精神。写作历史小说,也需要艺术的想象力,需要艺术的虚构。所以,在历史小说中,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给历史小说一具鲜活的肉身,对作者来说难度很大,同时也是一种写作道德意义上的审视与拷问。
小说有三个基本要素:交待环境背景,编织故事情节,营造人物形象。下面我从小说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情节,历史生活文化习俗等几方面,谈谈小说《风眼》是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和虚构的真实二者之间关系的。
小说《风眼》的环境坐标系是依据小城历史史实建构起来的。小说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俄边境小城绥芬河。绥芬河史称五站,是中东铁路中方起始铁路站。这个历史时期的小城商贸畸形繁荣,风云际会。居住和往来小城的有苏俄铁路员工,有口岸装卸码头工人,有身份复杂的各国商人,有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驻军,有闯关东的流民,有来往中东铁路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有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的隐秘战线上的工作者,有占领小城的日本侵略军,有抗日志士等等。
环境的塑造对于小说来说极其重要。小说中的环境交待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中自然环境的营造,可以为人物提供活动的地点、时间、场景等等。对自然环境的烘托,可以渲染气氛和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风眼》小说开场一段:“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秋天的脚步慢条斯理地盘桓在节气里迟迟不走。怎料西伯利亚的寒流说来就来了,且急不可耐地扑过了边境线。当呼啸的冷风横扫天长山密林,剥光树冠上颜色驳杂的叶子时,无尽肃杀寂寥的边城,竟颇有几分凛冬的寒意了。”这段统领全局的文字,不但交待了故事的时间、季节,小城的地理位置,而且通过对自然景观描写,也烘托了出场人物赵九龙的心理状态及整部小说的历史氛围,为这部作品奠定了冷峻的叙述基调。小说中社会环境的营造,可以为人物的出场和事件演绎提供一个可信的、复杂的、富于戏剧性的舞台时空,它能展示人物的身份、性格,推动人物行动等。比如作者在《风眼》小说中为赵兴东提供的社会环境:包括其家庭出身,去苏联接受特训,回到小城做人力车夫,暗杀日本兵,去外地做电工,去山东抗日,再回到小城侦察天长山要塞等,都恰如其分地营造了赵兴东的成长历程与行为动机,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
历史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尊重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允许做逻辑推理意义上人物性格的刻画。人物的真实与虚构如何拿捏到位,如何刻画精准对于作者是个考验。《风眼》这部小说中,赵兴东、李麻子等形象塑造较为鲜明。赵兴东是小城真实的历史人物,作者为表现赵兴东这一形象,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多次采访赵兴东的后人。正因为人物资料的翔实,在符合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的情形下,作者对赵兴东的言语、行动,内心世界进行了合理的想象与描写。从火烧赵家楼、穆棱电务段秘密接头、山东胶东抗日、天长山要塞智取情报等故事情节中,都能让我们感觉到一位勇敢、忠义、智慧、坚强的隐蔽战线工作者的清晰形象。李麻子的形象也非常鲜明,这也有其历史原型,正是他出卖了赵兴东。李麻子是那个时代胆小、自私、愚昧、麻木的一部分国人形象的写照。书中杨先生(杨明斋)的人物形象刻画及其后来的遭遇,都是尊重历史史实展开书写的,这位早期共产国际人物的形象,从言谈到举止都塑造得恰当得体。赵九龙、郭洪都、闫老虎、内田寿夫、赵夫人等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刻画,也很符合历史的真实状态,尽管他们多出于文学的虚构,但这种在艺术框架内虚构的真实,却给读者以深深的感染和审美的力量。
事件和情节是小说的筋骨和血肉。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的真实和虚构的真实时,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忠实于历史的真实,而具体的情节与细节在允许虚构的情况下,文本内在应该尊重历史行进的规律与本质,与历史时段的特征风貌相符合。《风眼》一书中,杨先生(杨明斋)从苏联境内进入小城,受到追踪袭击历险及取道上海秘密与老头子(陈独秀)见面;口岸装卸场南北码头帮派之争;日本福冈株式会社情报刺探;日军占领小城;日军宪兵队杀戮抗日志士;苏军攻打天长山要塞等重要事件及情节,都是小城那段历史的演绎与再现。小说中写杨先生从绥芬河取道上海,他在上海街头睹物回忆往事,都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可考。老头子(陈独秀)的言谈,也是依据了那个时代陈独秀对时局的主张,语出有据可依,并不是凭空臆想。日军天长山要塞的秘密修筑,要塞建筑情况,苏军攻打要塞等事件情节,也是依据历史翔实资料书写。即使小说中虚构的赵兴东深入要塞智取情报这一故事情节,读来也让人信服。事实上,当时日军要塞看管严格,除劳工和日军,外人几无进入的可能。为能让赵兴东进入要塞取情报,作者苦心经营设计了一番。作者在调查采访中,听本地一位电务段老人说,日军要塞曾经有电工进入修电。于是作者设计了阿福阿贵故意损坏要塞供电设备,日军请电务段工作人员去要塞修电,赵兴东才能得已蒙眼进入要塞,这符合事件进展的逻辑常识,也不违背历史的真实状态。赵兴东进入要塞修电时与阿福接头,取出情报如何带出也是个问题,因为日军进出严格管理。于是作者设计了阿福假装去厕所然后拉闸,赵兴东趁黑暗将情报装入鞋窠里这一幕。接下来作者让赵兴东再遇难题,出要塞要搜查全身,鞋窠里也要搜查,如何再过险关?这难题揪住了读者的心。作者又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环节,日军牵狼狗巡逻,急中生智的赵兴东故意踩上狗屎,然后去哨前检查,日本兵嫌鞋臭,摆手让他出去了。这些虚构的情节都符合历史的情形,也让人信服,巧妙得如同真实发生,这就是虚构的力量。
《风眼》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小城的日常生活、文化风俗书写,也竭力在呈现历史风物真实,对于其中日常器物,民俗文化,皆有精心的考证与描述。小说第一章作者营建的赵家大院,赵九龙书房的器物陈设,赵家主人及佣人的服饰,日常生活起居,能够让我们看到那时代小城官僚之家的状态,也折射了那时代上层人物的审美情趣。书中对小城梁家戏班的山东柳腔及演出唱词的书写,也呈现了小镇当时的文化风貌。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小城的建筑设施,上层人物的生日宴请,普通人日常、饮食,出行的交通工具,小城的估衣铺、豆腐坊、妓院、日式料理店、日军宪兵的行刑室等描写,都试图符合那时代小城生活的状态,这种具体历史语境的还原,使得其中的人物有了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在场保障,便于表现鲜明人物形象。
历史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非虚构小说。历史小说的真实性是历史性,合于逻辑的虚构性是文学性,这两个属性缺一不可。历史性需要作者有丰厚的历史知识,对所要书写的历史有深入研究,对历史有正确的评判。文学性需要作者有精心的构思谋篇,有风格鲜明的语言修辞,有精湛的艺术想象力,有真实的情感和思想深度。在历史小说写作中,能够平衡好历史的真实和虚构的真实,便可以给小说文本一具鲜活的肉身,也自然溢出小说文本中的灵魂。
小说《风眼》还有种种瑕疵,比如赵兴东在山东抗日一段略脱离主体内容,比如小说前半部分叙述的从容与后半部分叙述的仓促不一。尽管如此,但整体上看,《风眼》还是一部叙述性可靠且有血有肉的历史小说。





